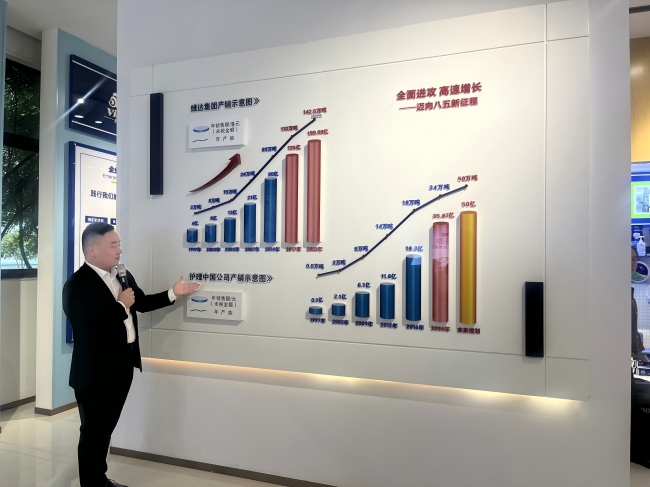д»ҠеӨ©дёҖеӨ§ж—©пјҢ家йҮҢдҫҝдј жқҘзҲұдәәзҝ»з®ұеҖ’жҹңзҡ„зӘёзӘЈеЈ°е“ҚгҖӮеҸӘи§ҒеҘ№е°ҶеӨ§йғЁеҲҶи–„ж¬ҫиЎЈжңҚеҸ ж•ҙйҪҗ收иө·жқҘпјҢеҸҲжҠҠй•ҝиў–дёҠиЎЈгҖҒеӨ–еҘ—еҸҠз§ӢиЎЈз§ӢиЈӨйғҪеҸ–еҮәжқҘпјҢж‘ҠеңЁеәҠдёҠпјҢеғҸжҳҜеұ•ејҖдёҖйҒ“еӯЈиҠӮзҡ„еҜҶд»ӨгҖӮзӘ—еӨ–пјҢжў§жЎҗеҸ¶иҫ№зјҳжӮ„жӮ„й•ҖдёҠдёҖеңҲйҮ‘иҫ№пјҢеҸ¶е°–жӮ¬жҢӮзҡ„ж°ҙзҸ еҝҪең°еқ иҗҪпјҢеңЁең°дёҠзўҺжҲҗеҮ з“ЈеҮүж„ҸгҖӮдә‘жўҰзҡ„з§ӢпјҢдҫҝеңЁиҝҷдёҖеЈ°иҪ»е“ҚйҮҢпјҢжӮ„然漫иҝҮдәҶе°ҸеҹҺзҡ„иЎ—е··гҖӮ

жё…жҷЁзҡ„и–„йӣҫиҝҳжңӘж•Је°ҪпјҢжҲ‘еҫӘзқҖеҹҺдёӯе„’еӯҰиЎ—йЈҳжқҘзҡ„йҰҷж°”иө°еҺ»гҖӮж—©зӮ№ж‘Ҡзҡ„зҷҪж°”д»Һз«№и’ёз¬јйҮҢиў…иў…еҚҮиө·пјҢйЎәзқҖйЈҺиһҚиҝӣжӣІйҳіи·Ҝзҡ„жҷЁе…үйҮҢгҖӮиҖҒеӯ—еҸ·вҖңдә‘жўҰзҢӘжІ№йҘјеӯҗвҖқй“әеүҚж—©е·ІжҺ’иө·й•ҝйҳҹпјҢеёҲеӮ…д»Һж»ҡзғ«зҡ„зӯ’зӮүйҮҢеҸ–еҮәж–°зғӨзҡ„йҘјеӯҗпјҢйҮ‘й»„зҡ„еӨ–зҡ®жіӣзқҖжІ№дә®зҡ„е…үпјҢеҲҡйҖ’еҲ°жүӢйҮҢе°ұзғ«еҫ—дәәиҪ»иҪ»и·әи„ҡпјӣе’¬дёӢдёҖеҸЈпјҢй…Ҙи„Ҷзҡ„еӨ–еЈіиЈ№зқҖзҢӘжІ№зҡ„йҶҮйҰҷпјҢзғ«еҫ—иҲҢе°–еҸ‘йә»пјҢеҚҙеҸ«дәәиҲҚдёҚеҫ—еҒңдёӢгҖӮ

дә‘жўҰзҡ„з§ӢеӨ©пјҢжҖ»еёҰзқҖзӮ№дёҚж…ҢдёҚеҝҷзҡ„иҜ—ж„ҸгҖӮж—ҘеӨҙзҲ¬еҫ—жңҖй«ҳж—¶пјҢж°”жё©д№ҹдёҚиҝҮдәҢеҚҒдёғе…«еәҰпјҢжҡ–иҖҢдёҚзҮҘгҖӮдёҚиҝңеӨ„пјҢеҹҺдёңжҘҡзҺӢеҹҺйҒ—еқҖзҡ„ж®ӢеһЈжөёеңЁжҷЁйӣҫдёӯпјҢжў§жЎҗеҸ¶иҗҪеңЁж№ҝж¶Ұзҡ„и·ҜйқўдёҠпјҢжү“зқҖж—Ӣе„ҝпјҢдјјжҳҜеңЁдёҺеӨҸж—ҘеҒҡжңҖеҗҺзҡ„е‘ҠеҲ«гҖӮйҳіе…үйҖҸиҝҮеұӮеҸ зҡ„ж ‘еҸ¶пјҢеңЁжўҰжіҪж№–зҡ„жұүзҷҪзҺүж ҸжқҶдёҠз»ҮеҮәж–‘й©ізҡ„е…үж–‘пјӣйЈҺдёҖеҗ№пјҢе…үж–‘дҫҝи·ҹзқҖжҷғжӮ пјҢеғҸж’’дәҶдёҖжҠҠи·іеҠЁзҡ„зўҺйҮ‘гҖӮжІіеІёиҫ№зҡ„иҠҰиӢҮдёӣе·Ій•ҝеҫ—жҜ”дәәиҝҳй«ҳпјҢзҷҪиҢ«иҢ«зҡ„иҠҰиҠұж”’еңЁжһқеӨҙпјҢйЈҺиҝҮж—¶пјҢдҫҝиҪ»йЈҳйЈҳең°иҗҪеңЁж°ҙйқўпјҢйҡҸжіўжјҫејҖз»Ҷе°Ҹзҡ„ж¶ҹжјӘгҖӮж№–з•”зҡ„еһӮжҹід№ҹжІЎдәҶжҳҘж—Ҙзҡ„еЁҮжҹ”пјҢжһқжқЎиў«з§ӢйЈҺжўіеҫ—жҹ”йҹ§зЎ¬жҢәпјҢеҚҙд»Қжү§зқҖең°жӢӮжӢӯж°ҙйқўпјҢе°ҶиҝңеӨ„ж–Үеі°еЎ”зҡ„еҖ’еҪұжҸүзўҺдәҶпјҢеҸҲж…ўж…ўжӢјеңҶгҖӮ

еҪ“ж—ҘеӨҙзҲ¬иҝҮдә‘жўҰеҚҡзү©йҰҶзҡ„иһӯеҗ»и„ҠпјҢй»„йҰҷеӨ§йҒ“зҡ„ж ҫж ‘е·ІжҠҠз»ҶзўҺзҡ„й»„иҠұж’’ж»ЎйҒ“и·ҜдёӨж—ҒгҖӮй»„йҰҷе°ҸеӯҰеҶ…пјҢз©ҝж ЎжңҚзҡ„еӯ©еӯҗ们иғҢзқҖд№ҰеҢ…и№Ұи·іиҖҢиҝҮпјҢжҢҮзқҖвҖңжүҮжһ•жё©иЎҫвҖқзҡ„еӣҫз”»еҸҪеҸҪе–іе–іең°дәүи®әвҖ”вҖ”иҝҷжҳҜеҲ»еңЁдә‘жўҰдәәйӘЁеӯҗйҮҢзҡ„з§Ӣж„ҸеҗҜи’ҷпјҡж—©еңЁдёңжұүгҖҠеҗҺжұүд№ҰгҖӢйҮҢпјҢвҖңжұҹеӨҸй»„йҰҷпјҢе№ҙж–№д№қеІҒпјҢзҹҘдәӢдәІд№ӢзҗҶвҖқзҡ„ж•…дәӢдҫҝдј дёәдҪіиҜқпјӣеҰӮд»ҠжҜҸдёӘз§Ӣж—Ҙзҡ„жҷЁиҜ»иҜҫпјҢж ЎеӣӯйҮҢд»Қдјҡе“Қиө·зЁҡе«©зҡ„иҜөиҜ»еЈ°пјҢдёҺж ҫж ‘зҡ„иҗҪиӢұдёҖеҗҢпјҢжҠҠеӯқйҒ“зҡ„жё©еәҰиһҚиҝӣз§ӢйЈҺйҮҢгҖӮ
еҫҖдә‘жўҰеҹҺиҘҝеҢ—иө°пјҢиҪҰиҝҮжё…жҳҺжІіеӨ§жЎҘдёҚеҲ°дёҖеҲ»й’ҹпјҢдә‘е®үеһёзҡ„еӨ©йҷ…зәҝзӘҒ然被ж’һејҖдёҖйҒ“йҮ‘й»„зҡ„еҸЈеӯҗвҖ”вҖ”иғЎйҮ‘еә—еҗ‘ж—Ҙи‘өиҠұжө·еҲ°дәҶгҖӮиҝҷдёӘең°ж–№жҳҘеӯЈиҝҳжҳҜдёҮдә©жІ№иҸңиҠұжө·пјҢзҺ°еңЁжҲҗеҚғдёҠдёҮж Әеҗ‘ж—Ҙи‘өпјҢеғҸиў«еӨӘйҳізӮ№иҝҮеҗҚзҡ„еЈ«е…өпјҢжӯЈйҪҗйҪҗжҳӮзқҖеӨҙгҖӮе®ғ们иҠұзӣҳжІүз”ёз”ёең°жңқзқҖе…үжәҗзҡ„ж–№еҗ‘пјҢиӨҗй»„зҡ„иҠұзұҪеңЁиҠұзӣҳйҮҢжҺ’еҲ—еҫ—з»ҶеҜҶ规ж•ҙпјҢд»ҝдҪӣзІҫеҝғи®Ўз®—иҝҮзҡ„жҳҹйҳөпјӣиҖҢиҫ№зјҳзҡ„иҠұз“Јд»ҚеҖ”ејәең°з•ҷзқҖзӣӣеӨҸзҡ„жҳҺй»„пјҢеғҸиҰҒжҠҠжңҖеҗҺдёҖзӮ№зғӯзғҲз„ҠеңЁз§ӢеӨ©зҡ„й—Ёж§ӣдёҠпјҢдёҚиӮҜиҪ»жҳ“йҖҖеңәгҖӮеҮ дёӘеӯ©еӯҗй’»иҝӣи‘өжһ—пјҢд»°зқҖи„‘иўӢж•°иҠұзӣҳйҮҢзҡ„зұҪпјҢе’Ҝе’Ҝзҡ„笑声еңЁз”°й—ҙеӣһиҚЎгҖӮ
йЈҺжҹ“жЎӮйҰҷзҡ„ж—¶иҠӮпјҢзӣӣз Ұжқ‘зҡ„жҷ’з§Ӣеңәе°Ҷ丰收й“әеұ•жҲҗдёҖе№…йІңжҙ»зҡ„ж°‘дҝ—з”»гҖӮзәўзәўзҡ„иҫЈжӨ’гҖҒж©ҷиүІзҡ„еҚ—з“ңгҖҒйҮ‘й»„зҡ„зҺүзұігҖҒзҷҪзІүзҡ„еҶ¬з“ңвҖҰвҖҰеҗ„ејҸеҶңе…·еҰӮиҖ•зүӣгҖҒйЈҺиҪҰгҖҒиҖ•зҠҒзӯүпјҢзҡҶз”ұеҶңдҪңзү©жӢјжүҺиҖҢжҲҗгҖӮи§Ӯе…үе°ҸзҒ«иҪҰиҪҪзқҖеҹҺйҮҢдәәз©ҝиЎҢз”°еҹӮпјҢиҪҰзӘ—жЎҶдҪҸжҷ’еңәе…ЁжҷҜпјҢжҒҚиӢҘеҫҗеҫҗеұ•ејҖзҡ„дә‘жўҰзүҲгҖҠиҖ•з»ҮеӣҫгҖӢпјҢи®©дәә们жІүжөёејҸжҺҘдҪҸиҝҷд»Ҫз§Ӣж—Ҙзҡ„жІүз”ёз”ёгҖӮ

жҲ‘еӣһеҲ°еҹҺиҘҝйҷ¶жҘјеә„еӣӯж—¶пјҢеӨӘйҳіжӯЈж…ўж…ўеҫҖдёӢжІүпјҢжҠҠжңҖеҗҺдёҖзј•йҮ‘иҫүжіјеңЁж°ҙйқўдёҠгҖӮж°ҙдёҚеғҸеӨҸеӨ©йӮЈиҲ¬ж»ҡзғ«пјҢеҖ’еғҸеқ—иў«жөёеҮүзҡ„зў§зҺүпјӣйЈҺдёҖеҗ№пјҢжјҫиө·зҡ„жіўзә№йҮҢжҷғзқҖеІёиҫ№жҹіж ‘зҡ„еҪұеӯҗпјҢиҝһеёҰзқҖйҷ¶жҘјзҡ„иҪ®е»“д№ҹеҸҳеҫ—жҹ”иҪҜиө·жқҘгҖӮй’“йұјзҡ„жұүеӯҗжҚўдәҶ件еҺҡдәӣзҡ„еӨ–еҘ—пјҢйұјз«ҝзЁізЁіж”ҜеңЁеІёдёҠпјҢйұјзәҝеһӮеңЁж°ҙйҮҢпјҢеҚҠеӨ©дёҚеҠЁдёҖдёӢгҖӮд»–еҚҙдёҚжҖҘпјҢжҢҮе°–еӨ№зқҖж”ҜзғҹпјҢзңјзҘһжңӣзқҖж№–йқўпјҢ讲究зҡ„жҳҜвҖңж„ҝиҖ…дёҠй’©вҖқзҡ„д»Һе®№пјҢд»ҝдҪӣй’“зҡ„дёҚжҳҜйұјпјҢжҳҜиҝҷз§Ӣж—ҘйҮҢж…ўдёӢжқҘзҡ„ж—¶е…үгҖӮ
еӨң幕йҷҚдёҙпјҢеҚҺзҒҜеҲқдёҠпјҢдә‘жўҰеҹҺеғҸжҳҜиў«з§Ӣе…үжөёиҪҜзҡ„з»ёзјҺгҖӮ银жқҸеҸ¶жү“зқҖж—Ӣе„ҝеҫҖең°дёҠиҗҪпјҢиё©дёҠеҺ»з°Ңз°Ңең°е“ҚпјҢеғҸи°ҒеңЁиҪ»еЈ°ж•°зқҖж—¶е…үзҡ„иҠӮжӢҚгҖӮеҹҺеҚ—еҗҙзҰ„иҙһдҪ“иӮІе…¬еӣӯдәәеЈ°йјҺжІёпјҢеӯ©еӯҗ们зҡ„笑闹声гҖҒиҖҒдәә们зҡ„и°Ҳ笑声пјҢж··зқҖжЎӮиҠұйҰҷпјҢеңЁжҷҡйЈҺйҮҢжј«ејҖгҖӮеҝҪ然пјҢе№ҝеңәиҲһзҡ„йҹід№җеҸҳдәҶи°ғпјҢгҖҠдё–з•Ңиө дәҲжҲ‘зҡ„гҖӢзҡ„ж—ӢеҫӢзј“зј“ж·ҢеҮәжқҘпјҢеӨ§еҰҲ们зҡ„еҠЁдҪңд№ҹи·ҹзқҖжҹ”ж¶Ұиө·жқҘгҖӮ

зҒҜе…үд»ҺжҘҡзҺӢеӨ©дёӢеӨ§иҲһеҸ°жј«иҝҮжқҘпјҢеғҸз§ӢеӨңжё©иҝҮзҡ„зұій…’иҲ¬пјҢзј“зј“жј«иҝҮе°ҸеҹҺгҖӮйЈҺеҚ·зқҖ银жқҸеҸ¶ж—ӢиҗҪж—¶пјҢзҒҜе…үжҒ°еҘҪиЈ№дҪҸеҸ¶зүҮзҡ„иҫ№зјҳпјҢжҠҠеҺҹжң¬жө…й»„зҡ„и„үз»ңжҹ“жҲҗжҡ–йҮ‘гҖӮеӨ§еҰҲ们ж‘Үж‘Ҷзҡ„иә«еҪұжӣҙдёҚеҝ…иҜҙпјҢжҠ¬жүӢж—¶пјҢиў–еә•жҷғеҮәзҡ„е…үеғҸжІҫдәҶжЎӮйҰҷзҡ„зўҺжҳҹпјӣиҗҪи„ҡж—¶пјҢеҪұеӯҗеңЁең°йқўиҪ»иҪ»еҸ еҗҲпјҢеҸҲйҡҸзқҖиҲһжӯҘж…ўж…ўиҲ’еұ•ејҖпјӣиҝһ鬓角еһӮиҗҪзҡ„еҸ‘дёқпјҢйғҪиЈ№зқҖдёҖеұӮиҪҜд№Һд№Һзҡ„жҡ–й»„пјҢд»ҝдҪӣжҠҠж•ҙдёӘз§ӢеӨ©зҡ„жё©жҹ”пјҢйғҪз»ҮиҝӣдәҶиҝҷе…үеҪұйҮҢгҖӮ
з§ӢеӨ©зҡ„дә‘жўҰпјҢжЎӮйҰҷ延з»ӯзқҖеӨҸеӨ©зҡ„зғӯзғҲпјҢзұізі•зҡ„з”ңйҰҷжүҝжҺҘдәҶиқүйёЈзҡ„дҪҷйҹөпјҢе°ұиҝһжһқеӨҙзҡ„иҗҪеҸ¶пјҢд№ҹеғҸжҳҘеӨ©зҡ„ж–°з»ҝйӮЈиҲ¬пјҢеёҰзқҖеҜ№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зҡ„зң·жҒӢпјҢиҪ»иҪ»иҗҪдёӢпјҢжҠҠж №жүҺиҝӣ家乡зҡ„жіҘеңҹйҮҢгҖӮ
пјҲи®°иҖ… йҷҲдёәиүҜпјү
дёҖе®ЎпјҡйҷҲиүі
дәҢе®ЎпјҡеҗҙдёҪеҗӣ
дёүе®Ўпјҡи”Ўе…ҙжңӣ